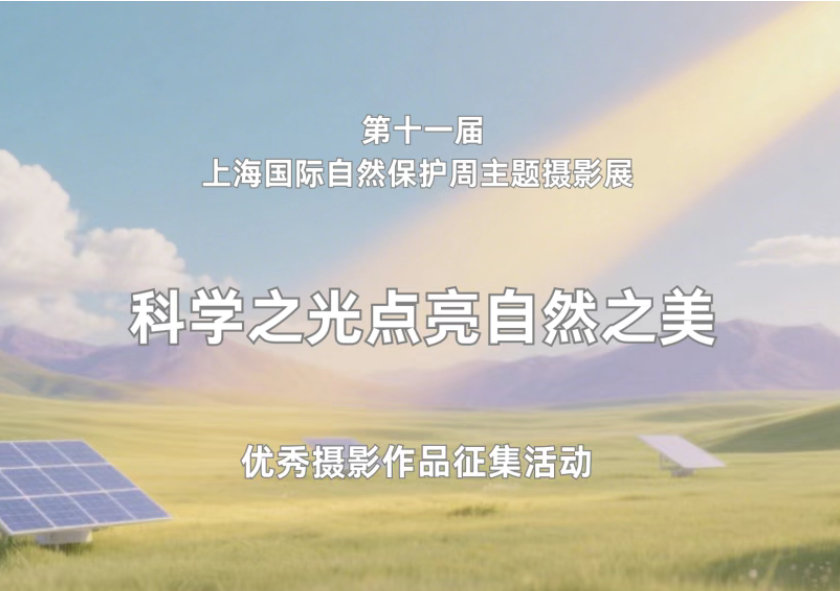大约无分东西南北,旧时中国的城镇之中,有两个大字大概是少不了的,一是 “當”、一是“酱”。一般皆是用正楷写在当街大门旁的白粉墙上,而且字大得惊人,再深度的近视眼也不难看到,即使一字不识之人也知道这两个字一是当舖、一是酱园的符号,因为这两个行当从事的是关系民生之事。
当舖可以以物抵押贷款。不过,走进当舖必是无奈之举。去酱园则是为了日常生活的“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兵荒马乱之时,亦不论贫穷、富贵,皆是需要的。所以无论是帝王之都、通商大埠、还是边城小镇,这酱园皆是少不了的。十里洋场的上海也不例外。最近就有一个名为“酱园弄.悬案” 的电影热演,便是描述了民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一条因设有酱园而得名的弄堂里发生的故事。
酱园多为前店后作坊的形式,主营各种调料与酱菜。记得上个世纪40年代读小学时,国文课本里就有一篇关于酱油的课文,说是在美国某地的唐人街上,洋人都觉得中国餐馆的菜肴可口。但一日他们看到厨师向菜中倒了一种黑色的液体,以为不卫生,而不再去用餐了。店主无奈只得将此物送验,结果证明此物名为酱油,由大豆制成,不仅卫生而且营养丰富,从此中餐馆生意兴隆。所以一直记得洋人不会做酱油之说,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出国,关注了一下,果然西洋人原本确实不会做酱油和醋,当然也没有酱菜,他们吃一种酸黄瓜是用柠檬汁泡出来的。
也不只是西洋人不会做酱菜,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初,家父的一个经营酱园的朋友来谈起,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曾去支援边疆建设,在新疆发现维族同胞的酱菜 “死咸、死咸”,原来他们只知用盐腌,不知其他,乃授以加 “甜蜜素” 调味之法,果然口感大好,维族同胞大喜。也算是民主党派同志支援边疆建设的一份贡献云云。
其实,酱菜的特点即在于“咸”,入口便有了一个咸的感觉,让人感觉“有味”,故大多数菜肴烹制过程中皆需加点盐。当然,摄入适当的盐也是人体生理之必须,即使洋人的餐桌上也有盐瓶,可供食者随时取用。但是 “太咸” 的感觉並不妙,于是便用吞饭来缓和,这样一来却产生了 “下饭” 的作用。富裕阶层自不靠此下饭,而且下不下饭,对于食物丰富的富人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但对于旧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民众来说,能否下饭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比如过去形容做学徒的人要 “吃三年萝卜干饭”,便是指学徒的生活困苦,靠萝卜干下饭度日之事。
如今我国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为促进健康计,须得讲究饮食的科学性,因此便有了(减油、减盐、减糖)“三减”的要求。我国民众素重口味,盐的摄入量远超每人、每日不超过5克的规定。与此同时,我国高血压病的发病率亦居世界第一,盐的摄入过多与此病发生的关系是肯定的,而且欲控制高血压,控制心力衰竭、肝硬化腹水、肾性水肿等等,皆需控制盐的摄入。我曾见过一位高血压病患者,同时服用三种降压药物皆无效果,被诊断为 “难治性高血压”。我劝他要尽量吃得淡些,患者笑而不语,他的夫人在一旁抢白道:我家老严一个礼拜要吃掉3、4瓶酱菜。如今要吃这么多酱菜的人并不多见,但因吃得太咸而影响高血压控制的却大有人在。
从食品科学的角度来看,酱菜应不属 “高营养密度” 的食物,酱菜虽由青菜、萝卜、黄瓜等制成,但因盐的含量过高,在“可接受的盐量” 的前提下,通过食用酱菜得到的其他营养素就少之又少了。所以极需要推出 “低盐酱菜”系列。不过,从科学的饮食理念来说,更应该提倡食用新鲜的食品。
当然,酱菜并非不可以吃,风味食品偶尔食用亦添乐趣。最近“苏超” 足球火热,常州队球踢得不怎样,常州商业部门却推出 “萝卜干炒饭” 以慰球迷之情,蓋因常州所产之萝卜干素有盛名,倒也罢了。
作者与公众号简介
本文作者杨秉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复旦大学中山医院院长、上海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等职,因肝癌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